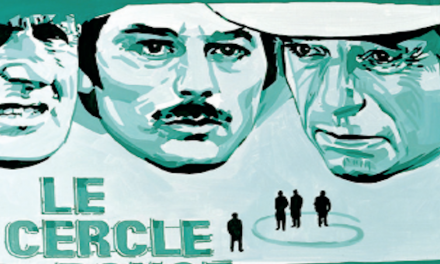? 阿信?(筆名) |資深投資人
【導讀】 如何理解中國的治理邏輯?為什么中國沒有像西方預言的那樣崩潰,反倒取得巨大成功?為什么統一對中國如宗教般重要? 為什么在中國治理結構下,能夠實現和平與發展,并朝著共同富裕邁進?為什么中國的復興是歷史性的而不是偶然性的?
本文 從治理邏輯與治理結構出發,討論和回答了上述問題。 作者指出,過去2000年來中國所有的制度設計和治理邏輯,都圍繞國家統一、天下太平這個目的而展開,直至今天。 天下為公的政治理想從周公到孔子,經過數千年來億萬人民的實踐和腥風血雨的打磨,早已成為中國治理邏輯的潛意識。表現 在傳統制度上,就是天子與流官共天下:前者應該代表最廣大人民的長遠利益——統一、發展和共同富裕,后者 則從垂直和水平方向實現了公平和廣泛的代表性 。 今天,中國的基本治理框架仍遵循這一軌道,但新中國對治理邏輯的升級是全方位的。其中突出的一點,是中國共產黨建立了具有高度組織性,充滿活力,能夠代表人民長遠利益的政治組織。
作者認為,從歷次盛世的規律來看,我們這個盛世才剛剛開始,只要實現統一,不內亂,盛世就能長期保持下去。因為天子流官體制本身具有自我糾錯能力,“改革開放”更為克服大一統體制的僵化注入了新動能。他認為,改革開放應該理解為“用開放的心態去適應”。改革的核心是批判教條主義,制度一定要不斷適應變化的世界,只要是有效的制度就學習,不封閉自大,才能引領世界的變化。在此意義上,改革開放就是制度本身。
本文為文化縱橫新媒體“歷史觀察”專欄特稿,原題為《中國的治理邏輯》。感謝作者授權原創首發,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諸君思考。
中國的治理邏輯
▍地獄和天堂之間是一個有效的政府
講一個小國的故事,非洲的盧旺達。
我在上海辦公室要安裝一臺新電腦,來服務的IT工程師是一個非洲黑人。小伙子中文講得很溜,技術熟練。一問,老家盧旺達。除了感嘆上海的國際化以外,我也對盧旺達發生了興趣。
盧旺達是中非小國,沒礦,沒油,連出海口都沒有,完全沒有存在感,是一個絕大多數人在地圖上都找不到的國家。但是這個國家在1994年一夜成名,在一百天里一百萬人被屠殺,占全國人口的八分之一。每天一萬人被殺,而且大多是以砍刀砍頭的方式進行的。人們揮起屠刀殺死他們的鄰居、同學、同事,甚至家人。腥風血雨,人間地獄。
快進到2019年,盧旺達GDP增長9.4%,世界第一。而且從2000年到2019年20年間,平均GDP年增長率超過6%。貧困率降低一半,人均預期壽命從25歲提高到64歲。營商環境評分全球排名第38名,超過荷蘭。首都基加利是非洲最安全的城市。基礎設施在非洲首屈一指。普及了義務教育,全民醫保。婦女地位大大提升,婦女在議會中占比超過60%,世界第一。雖然依舊貧窮,但充滿希望,盧旺達在非洲是天堂一樣的存在。
二十年從地獄到天堂,到底發生了什么?
謎底大概來自一個人——現在的領袖卡加梅。六年間,他領導的團隊從難民營打回盧旺達,奪取政權。在中部非洲打了個地區大戰,戰無不勝,為盧旺達贏得了一個獨立和平的外部環境。卡加梅從2000年開始正式擔任總統。政治上消除民族差別,建立強力、廉潔、高效、為人民謀福利的政府。經濟上改革開放,引進外資,建設基礎設施,制定符合本國國情的經濟發展戰略。
故事聽起來是不是有點耳熟?事實上盧旺達和中國關系非常好,基礎設施基本是中國幫助建設的,連閱兵儀仗隊都是中國幫助訓練,喊中文口令。 現在可以理解為什么一個盧旺達小伙子可以講著流利的中文,為我在上海裝電腦了。
過去20年,我跑了世界上60多個國家,看風土人情,聽他們的故事,思考中國的事情。回首看來,各國命運起起伏伏。從天堂到地獄,從地獄到天堂。
我總在思考一個問題:一個國家最寶貴的資源是什么?絕對不是石油,不是礦產,不是關鍵的港口和運河。這些年來我越來越堅信,地獄和天堂之別,就在于是否有一個有效的政府。
卡加梅可以在一代人的時間里把盧旺達變成非洲的榜樣,李光耀可以把彈丸之地新加坡變成世界的榜樣,而我在有生之年看到了,通過100年奮斗,40年改革開放,中國共產黨把一個本來在亞洲都出不了線的中國,帶進了決賽,可以和美國爭奪世界冠軍。反觀無效的政府讓阿根廷抱著金飯碗討飯吃,讓流淌著石油的尼日利亞沒油可加,無政府的索馬里繼續在絕望中掙扎。
可見,能否建設有效的政府,是走向和平發展的幸福之路還是墮入危險、絕望的地獄之門的關鍵,值得仔細探討。那么什么才是有效的政府,如何評價一個政府是否有效?
我的職業是管理企業,評判一個企業管理的好壞只有一個標準,看業績。而評判一個管理人員的表現,看KPI。但一個國家政府的好壞怎么評價呢?
拋開復雜的政治理論,我認為衡量一個有效政府應該有三個主要指標:和平穩定,經濟發展,共同富裕。這三個指標互相依賴,互為條件。穩定為發展創造條件,發展為共同富裕創造條件,共同富裕才能長治久安。不論理論家、政治家講什么神圣的理論,普通人需要的是柴米油鹽,是成家生子,是生老病死。不能讓絕大多數人民普遍富裕、生活越來越好的政府就不是有效的政府。
在最近一次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上,韓國被正式列入發達國家行列。這是自1964年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成立以來,首次有國家從發展中國家“晉升”為發達國家。六十年只有一個畢業生,只能說到目前為止,發展中國家復制西方發展模式的企圖并未成功。
拋開所有口號,拋開意識形態的借口,用實事求是的方法給有效性打分,結果一目了然。
問題是為什么會有這樣的結果呢?各派有各派的說法:人的問題,政策問題,文化問題,等等。里面有沒有治理邏輯的問題呢?
▍ 天子治下的和平
美國認為自己享受特殊地位的原因是它提供了全球的公共產品——美國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美國作為世界警察,在二戰后特別是冷戰后,維持了世界近40年大體上的和平。所以美國可以不參加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但要求別人遵守;美國可以發美元向大家收鑄幣稅,因為養警察要收稅……
Pax這個說法最早來源于羅馬治下的和平(Pax Romana),專指從公元前27年屋大維建立羅馬帝國到奧留良皇帝在位的200多年,那是地中海世界基本沒有戰爭的黃金時代。從那以后,歐洲人的夢想就是回到羅馬,重享百年和平。所以中世紀有神圣羅馬帝國,德國皇帝也自命為凱撒,俄國沙皇的“沙”也是凱撒,大英帝國也要做羅馬,美國就是羅馬的翻版:回到羅馬是歐美的政治理想。
但是羅馬以后再無羅馬。歐洲在羅馬帝國以后再也沒有享受過百年和平。 整個大陸分裂成了無數小國,戰爭不斷。中國歷史上,最慘烈的時期是春秋戰國500多年,戰爭連綿不斷。特別是戰國時代,動輒斬首以萬計。長平之戰,趙國被殺40萬戰士,一代青壯年基本全部被殺。在殺戮的血海里,古人深刻地意識到和平才是全體人民最大的利益。因為沒有和平就沒有生存。
要實現和平就必須統一。
沒有統一就沒有和平,沒有和平就沒有生存。覆巢之下,沒有完卵。
和歐洲不同,從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統一中國到1911年約2200多年間,我們合多分少,實現了1600多年的統一和平,占比超過80%!我們不但有第一個羅馬——漢朝,還有隋唐、宋元、明清,而且不僅僅是一個國家的統一,這是天下太平,包括了古人能力所及的世界,周邊的民族,都基本實現了和平。
在羅馬之外的世界還存在一個在比羅馬面積更大,人口更多的天下太平:天子治下的和平 (Pax Sinica)。
2017年夏天我周游歐洲,一口氣去了15個國家。這些所謂“國家”,大的如英國,只相當于廣東省,小的如馬其頓,是一個小縣。瑞典800萬人口,相當于徐州。如果以此類推,中國可以有20個左右英國一樣的大國,可以再分成約150個瑞典一樣的中等國家,1000個以上類似馬其頓的小國。
所以西方人很難理解中國的治理邏輯。很難理解為什么統一對中國那么重要,因為人類歷史上除了華夏,從來沒有一個民族把億萬人民同化,認為你我他屬于一個國家,我們都是兄弟姐妹。這是一個獨特的存在。
過去2000年來中國所有的制度設計、治理邏輯都是圍繞國家統一、天下太平這個目的在展開,直到今天。
所以要拋開西方的政治概念和理論來理解中國的治理邏輯。近代的生搬硬套造成了西方人對中國的誤解,造成了中國人自己的迷惑。
那么我們的先人是如何做到天子治下的和平的呢?
▍ 統一從思想開始
美國號稱“Melting Pot”,民族熔爐。所有人到美國都最終變成了美國人。其實中國才是歷史上最大的民族熔爐。所有進入中國的民族,都最終成為了中國人。從最早的東夷北狄南越,到匈奴鮮卑羯氐羌,再到突厥契丹和女真,都在這個大熔爐里混合成為一體。
美國是個現代移民國家,可以依靠科技手段來洗腦,實現國家認同。中國古人在交通基本靠走、通訊基本靠吼的年代,是怎么做到讓億萬人民形成文化認同,成為一個民族的呢?
(一)書同文
美國CIA評外語難度,漢語一直是最難學的外語之一。漢字是所有主要語言中唯一一個非字母文字,連古埃及象形文字,那些好看的圖畫,也是字母。學習漢語,沒有捷徑,必須記住幾千個字才能讀書,所以我們小學語文的主要時間都在練習默寫。圣經上說上帝為了懲罰亞當夏娃,讓他們的子孫在地上說不同的語言,不能溝通,所以他們就自相殘殺。
不知是有意為之,還是運氣使然,我們的祖先為一個大陸的人民創造了一個可以互相理解和溝通的工具,破了這個咒語。雖然語言不同,但大家認同樣的字,讀一樣的書,就有了同樣的思想。一紙政令可以天下通讀。因為有統一的文字,各地的語言就變成了“方言(Dialect) ”,而不是獨立的“語言(language)”。如果是字母文字,各地的人就會用字母拼寫自己的語言,開始讀不同的書。人們不能交流,沒有認同,自然會四分五裂,如歐洲。
所以過去知識分子最重要的能力是會寫文章,考試最重要的內容是制式寫作——八股文,因為重要工作的主要溝通工具是文字而不是口語。就像我早年到日本,日語不會,碰上不講英文的日本人,急了可以筆談。一個統一的、不能本地化的文字,成為文化認同的核心工具——或許可以解釋為什么中國要急于發明造紙和印刷術了。
過去150年有很多人想把漢字拼音化,而且也發明了拼音,但是一直搞不成。因為文字拼音化就是國家分裂的開端。所以漢字可以簡化,不能拉丁化。
共同的文字又促進了共同語言的形成和保持。從周朝的雅言,到洛陽官話,到今天的普通話,讀書人都能掌握和書面語言一致的官話。讀書人又慢慢帶動民間。
共同語言、共同文化傳統為統一民族的形成和天下的統一奠定了文化基礎。
?
(二)以人為本
2011年我第一次到埃及,和朋友的孩子聊天,她問我一個問題: What’s your religion? 你的宗教是什么?我不知道怎么回答。她拿出身份證給我看,其中有一欄是宗教,人人必有宗教,就像要填性別一樣。我說我沒宗教,驚得孩子目瞪口呆。
對于大多數中國人來說,宗教是一件很私人,甚至很遙遠的事。雖然偶爾也會拜神佛求保佑,但西方意義上的宗教從來沒有成為人們生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也從來沒有成為政治制度的一部分。中國人把生活在世俗的世界里當成理所當然,但在歐洲歷史上,政教分離是件了不得的事。
為什么會是這樣呢?儒家沒有上帝,佛祖也是個凡人。中國人怎么解決終極問題?你從哪來,到哪去?如何面對死亡呢?
其實中國在商朝時非常信鬼神,殺活人祭祀。后來出了個周公,他利用周滅商的機會,拋棄了鬼神崇拜,建立了世俗的人文主義信仰。這種信仰簡單說就是,人活著是為了人而不是為了神。
所以“人命關天”,所以孔子說:“敬鬼神而遠之;不知生,焉知死;不能事人,焉能事鬼。”
這里的“人”不僅僅是個人,而是一個家族,一個民族乃至全人類。 邏輯非常簡單,我們都從祖先那來,到子孫那去;人死后回到了祖先那去,香火由子孫傳承。人作為個體會死去,但是作為一個整體會永生。
所以傳統的中國文化中,葬入祖墳,進入宗廟,有兒子年年祭祀是人生最重要的追求。所以不孝有三,無后為大。一個傳統的中國人,沒有兒子就在宗教意義上永遠死了。所以中國人最惡毒的詛咒是讓人家斷子絕孫。所以計劃生育如此之難,生男生女不是個經濟問題,而是個宗教性質的問題。
所以個人利益要服從集體利益,因為人生的目的是家族,是種族,是人類的血脈傳承,而不是為了自己享受; 所以孔子說殺身成仁,孟子說舍生取義。 犧牲自己,為了大家 ; 所以疫情來了,該封城封城,該隔離隔離,該掃碼掃碼。 因為整體生存大于個人自由; 所以中國人最愛記歷史,從公元前800年開始,2800年來每一年都有文字記載。 因為歷史傳承就是信仰的傳承。
這個邏輯如此簡單易懂,同時和國家治理、日常生活結合得如此緊密,成為抵御外來宗教的強大力量。
中國人對政府的期望很簡單——和平安定,經濟發展,共同富裕。能夠讓子孫繁衍,讓人類永生。
(三)天下為公
1982年,中國共產黨“十二大”正式提出到2000年實現“小康”的目標。當時大家對什么是“小康”一頭霧水。我那時剛上初中,我們一個語文老師賣弄學問,給我們抄了一段當時很難看到的話。多年后想起來,再翻出來看,有一種石破驚天的感覺——
“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惡其不出于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
今大道既隱,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為己,大人世及以為禮。城郭溝池以為固,禮義以為紀。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設制度,以立田里,以賢勇知,以功為己。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于禮者也。以著其義,以考其信,著有過,刑仁講讓,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勢者去,眾以為殃,是謂小康。”(《禮記·大同篇》)
原來“小康”是2000多年前《禮記》中記載的教導。再聯想到孫中山先生寫的“天下為公”,聯想到“世界大同”,聯想到為人民服務,聯想到扶貧,聯想到人類命運共同體,聯想到共產主義理想,會發現這就是中國傳統的政治理想。 這個政治理想是維持這個制度的精神力量,因為只有堅信自己掌握真理的人才能領導人民。
這個政治理想不是高貴地為了實現神的天國,而是謙卑地為了人民能過上好日子;不是為了某個階層的私利,而是為了實現所有人的平等和長遠利益;這個理想是對最弱勢群體的關懷;這個理想體現了自然法則下的秩序;這個理想如此樸素,又如此親切。
這就是中國制度的道統。相當于憲法的序言,或美國的獨立宣言。這個道統從周公到孔子,再通過2500年,經過億萬人民的實踐、腥風血雨的打磨,已經成為了中國治理邏輯的潛意識。 不論是誰當政,向著這個方向前進,就國泰民安,最終走向勝利;偏離了這個方向就會被歷史拋棄。
▍ 天子與流官共天下
在傳統中國的治理體系中,有三種力量互相制約:天子、流官和百姓。
在中華文明里,天子一直是正面的、文明的象征。五四以來對傳統文化矯枉過正,把天子等同于皇帝,等同于昏君,再等同于專制和落后。實際上,天子一方面是皇帝本人,另一方面是一個機構化的存在,代表了法統,是政府合法性的來源。
天子應該代表最廣大人民的長遠利益——統一、發展和共同富裕。 開國天子的產生是通過最激烈的競爭——戰爭的方式產生的,勝利者是最有才能,獲得最多支持和運氣最好的團隊。執政的初始合法性來自能夠重新統一,實現天下太平,持續的合法性則來自發展經濟,人民有基本的生活保障。
天子和百姓的利益是一致的,因為如果百姓不滿意,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天子就失去了合法性,就會被推翻。
官僚往往追求的是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所以總有貪官欺壓百姓,總有天子懲治貪官。古往今來,中國可能是全世界懲治官員最多的國家。
天子、官僚和百姓三者形成了一個動態的平衡。所以孟子說:“民為重,社稷次之,君為輕。”所以宋江反貪官不反朝廷。
但是只有天子也不行。漢高祖感嘆,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其實更大的問題是安得文士兮治國家。怎么才能長期有效治理如此之大的國家, 促進融合而不是分裂呢?
羅馬以后,歐洲是教皇下面的封建貴族制。一層一層世襲貴族,有點現在承包制的味道。好處是管理半徑小,成本低。壞處是沒有真正的統一,一言不合就開打,征戰不休。
從秦朝開始,中國獨創了一個制度——流官制度,解決了這個問題。 流官制度顧名思義,是官員要流動起來。 各地的官員由中央統一選拔、任命和考核,并且不斷輪崗。基本上一個地方的主要官員都不是本地人。 通過流官制度,可以消除地方勢力,使精英階層互相交流融合,形成統一的核心團體和力量。
以明朝著名清官海瑞為例,生于海南,先后在浙江、江西、云南、北京、南京等地任職,最后死在南京。那可是每一步都要靠雙腿行走的年代!中國人習以為常的方法,在歐洲很難想象,一個意大利西西里人,可以在德國、法國、瑞典、倫敦做官,最后死在維也納?
流官制度聽起來很豐滿,但現實很骨感。第一個實驗這種制度的是秦朝,秦始皇派秦吏到新建的郡縣做官。這些外鄉人很快被殺,被趕走,秦也隨之滅亡。
要想流官制度長期有效,就要滿足以下幾個條件:一 、能夠選拔和培養足夠多的人才;二 、這些人能夠有共同的意識形態、通用的溝通和管理技能;三 、能夠代表所有地區,實現地區間的平衡;四 、能夠以公平的方式選拔精英,讓社會各階層認可。
秦朝的經驗表明,靠一個地區的干部管理全國并不可行,所以漢朝進行了第一次大的改革,實行推舉制,后來改成察舉制。各地郡守推薦孝廉、秀才等,中央考核,在太學學習培養,然后任命官吏。這個制度滿足了前三個條件,奠定了大一統的基礎,讓漢帝國統一了400多年。
但是這個制度最大的問題是推薦標準不統一,推薦變成了利益交換,形成了新的貴族制度——門閥士族。這些家族在地方上控制一方,在中央彼此交換利益——有點像現在的菲律賓——所以才有了袁紹家四世三公的局面。
從隋朝開始的科舉制度終于堵上了最后一個漏洞。科舉打破了人類歷史上最普遍存在的血統制,讓所有人,基本上(當然有例外)不分民族、種族、階級、財富都可以按照公開透明的方式,靠自己的努力進入政府,成為社會精英,向上參與治理國家,向下提升自己和家族的社會地位。 所謂“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
這個制度如此有效,獲得人民如此擁戴,以至于在中國過去1000多年變成了宗教一樣的存在,對考試公平的追求到了極致。為了保證公平,甚至犧牲了內容。后人對八股文口誅筆伐,但是想當初八股文是最公平的。
首先,這是標準化考試,標準統一。而且只考四書五經,使學習成本最小化。窮人家只要能買得起幾本書,一共就幾萬字的材料,努力就有機會。如果像現在的素質教育,鋼琴、冰球加慈善,科舉就又回到了漢代的察舉——所以批判衡水中學要小心。所以過分的補習班和貴族學校最終都要受到打壓,因為差別教育讓階層固化,動搖國本。
在中國,能和美國大選媲美的全國性動員是高考。那三天全國干部、警察加班,父母請假,白天汽車不能鳴笛,微信朋友圈刷屏。考試才是中國的選舉。
標準化考試只是實現公平的第一步。為了保證地區代表性,中國進士名額按省份,大體按人口分配。從發達地區到落后地區參加考試是嚴重的犯規行為。聽起來是不是耳熟?以人口比例分配名額,以統一考試為選拔標準的制度,選出了具有廣泛代表性的精英領導國家。
考中只是進入體制的開始,與之配套的是嚴格的培養考核制度。從宋開始,中國政府一直都有完整的基于KPI的考核培養制度。官員基本上要從縣官開始,不斷磨練,定期考核。而且從發達地區到不發達地區,從地方到中央,從司法到行政,不斷輪崗。能當上宰相的都是百煉成鋼的政治家。
在這個基礎上,基層考試選拔的秀才和退休的官員形成了鄉紳階層,代表本土利益,和流官制度互相制約,也互相補充,形成了穩定的結構。有點像今天以政協為核心的統一戰線制度,把體制外的精英也團結起來。
這個制度如此合理,由哲學之王做天子,不分階級出身,以公平的考試選拔人才,簡直和柏拉圖的理想國暗合,成為17世紀歐洲反對貴族和教會統治的榜樣。按照伏爾泰的說法,中國是那個時代的燈塔國。套用現代西方的術語,這個制度是另外一種模式的民主制度,因為這個制度從垂直和水平方向實現了公平和廣泛的代表性。
▍ 像麥肯錫一樣治理中國?
做投資時間長了,每天研究公司治理結構,發現治理結構好的公司業務不一定好,但治理結構出問題的公司業務一定不好。如果把國家比作公司呢?
一個極端是美國。美國政府就像美國的公司一樣,可以算是沒有大股東的上市公司。選民就是股民,股東大會選出董事會就是國會,請個CEO,就是總統。大家都是專業人士,透明、法治、按規矩辦事,看起來很好。但是這個制度的問題是股東缺位,內部人控制,管理層自肥。
另一個極端是沙特,純家族企業。一個股東,國名都是他們家的姓,基本是家族成員管理國家。家族企業的好處是,自己的產業會比較在意,決策比較快,但碰到差的繼承人就會垮掉。
基本上所有國家都能由此類比。有人問新加坡算什么?答:上市的家族企業。雖然是家族企業,但因為上市,更透明,有規則,而且能夠吸引比較好的人才參與管理,再加上規模小,非常有效。
那問題來了,中國屬于哪種?肯定不是美國意義上的上市公司,也一定不是家族企業。我們平時看公司看多了,其實有另一種治理結構非常普遍,那就是合伙人制度。所有的會計師事務所,律師事務所和大多數顧問公司都是合伙人制度。最典型的就是我服務過的麥肯錫咨詢公司。
麥肯錫是1926年由麥肯錫先生在美國創立,迄今已95年歷史,是世界頂級的管理咨詢公司。全球員工有30000多人,每年收入超過100億美元。麥肯錫已經成為卓越管理的代表,這樣一個組織,居然沒有公司意義上的股東,和麥肯錫先生除了名字以外沒有任何關系。麥肯錫治理結構的特點是:
初心不變,客戶第一(Client First)。 以為客戶解決重大戰略問題為宗旨。靠理念而不僅僅是錢來激勵員工。
組織統一(One Firm Policy)。 麥肯錫的工作方法、交流語境、科技手段等全球統一。把一個人從莫斯科派到北京,接上電腦就可以加入團隊,開始工作,基本沒有違和感。
內部培養。 主力的咨詢顧問是大學或MBA畢業,直接加入,不斷淘汰,培養。最后成為合伙人。基本不在外面招聘經理以上的人員。
任人唯賢。 嚴格的按能力(meritocracy)的全方位考核,按照結果晉升或淘汰。
注重培訓。 除了日常繁多的培訓外,每個重要級別的提升,都有專門的脫產培訓。
注重調研。 重要決定要反復調研。記得2002年非典,公司要節約成本,在選擇長途電話加密碼(可以降話費),還是減少晚餐補貼上,還進行了專題調研,發明了痛苦指數。結果是,長途電話加密碼,對每天要打很多電話的同事來說痛苦指數非常高。而每天50美元的晚餐補貼,完全是按照美國標準,在中國可以請一家人吃飯了,所以改成15美元,基本無感。
集體領導,協商決策。 重要人事任命和決策在合伙人之間充分醞釀,形成共識后決定。因為沒有股東,合伙人大都利益一致,內部可以吵,但對外很團結。所以決定的過程看似有點亂,不透明,實際上總能醞釀出對公司最好的策略。即使有錯誤,也能及時糾正。
這樣一個靠人和的組織,歷經近百年,人換了很多代,依然不斷壯大,生機盎然。
另外一個非常成功的合伙人組織是羅馬教廷。1700多年來,教廷經過無數風雨,但作為一個組織能夠不斷變化,適應環境,到今天依然生機勃勃。仔細看教廷的組織結構,也是典型的合伙人制度。保持信仰的初心,建立統一的組織,團隊自己培養,任人以能,雖然不透明,但總是能夠通過內部醞釀形成合理決策。內部不管聲音多么不同,對外總是很團結。
看起來是不是眼熟?中國共產黨的組織型態,和麥肯錫有很多類似之處,非常像一個合伙人制度:
不忘初心,注重思想工作,以理念激勵;
組織統一,可以把干部從內蒙調到廣東,毫無違和感;
內部培養,核心的干部全部是工作就入黨,經歷沒有斷層;
嚴格的組織培養、考核、提拔制度;
提拔之前上黨校;
沒有調察就沒有發言權;
集體領導,重大決策靠醞釀,協商,達成一致;
內部有不同意見可以討論,但對外團結 — —總有人將此視作所謂黨內斗爭,黨要分裂。殊不知,這是合伙人制度的特點和優勢。
閱讀現在西方主流的媒體,世界變成了黑白的,不是民主就是專制。其實西方最有效的治理模式也是某種合伙人制度。 在羅馬是元老院;在美國是精英合伙制,就是川普提到的華盛頓內部人(Washington Insiders);在日本是東京大學畢業的前貴族的后代;在韓國是政法培訓班畢業生;在英國是貴族里的牛劍畢業生;而在法國,歷屆總統都出自戴高樂創建的法國行政學院……
中國共產黨吸收列寧主義,建立了有高度組織性,充滿活力,能夠代表全體人民長遠利益的組織,面對3000年不遇的變局,把中國帶出了亂世,重新回到和平發展和共同富裕的軌道上。
▍盛世還能走多遠
2016年,一個朋友公司搞年會,請我做嘉賓。他們的規矩是所有嘉賓只能講業余愛好,不能講和自己專業有關的話題。所以,我就不能講投資,于是選了個我業余愛好的歷史話題:“盛世還能走多遠”。
歷史上的盛世就是國家統一安定,人人有工作,有飯吃,弱勢群體得到照顧。以此為標準,201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時就已經是盛世了。
那這個盛世還能持續多久呢?有人天天喊“中國崩潰論”,我們這一代未來會在盛世里享受生活,還是將在亂世中掙扎?
我喜歡年代數字,愛看中國歷史年表,看到一個很有意思的規律。從秦開始,中國王朝的演變規律,基本上是先有一個短王朝或動亂,然后再統一成為一個長王朝,開始進入盛世。長王朝持續大約250-300年。而且長王朝也有規律,一般是開國皇帝非常強勢,但在位20年左右,晚年會有一個動亂期。第二個皇帝比較弱,如果挺過來,大概有100年的和平盛世。
秦是短王朝,只有14年。漢是長王朝,西漢東漢和平時期加起來超過350年。劉邦死后,惠帝時呂后專權。從文帝開始,文景之治,再加上漢武帝,一共93年,祖孫三人創造了大漢的頂峰。中間王莽篡位,但很快就光武中興。
漢末動亂了36年后曹丕稱帝,進入三國時期,又過了60年到西晉統一。但這個時候,歷史出了軌。西晉第二個皇帝晉惠帝是個弱智,沒熬過去,造成了八王之亂、五胡亂華,一下動亂了300多年。
隋朝統一37年,是個短王朝,然后是大唐,統一了289年。唐太宗算是第一個真正統一的皇帝,他死后高宗弱,武則天當政,亂了一段時間。直到唐玄宗政變上臺,一口氣統治了50多年,有了開元盛世。然后是安史之亂和藩鎮割據,但基本上維持了100多年的和平。
唐之后是五代十國,大概50年。然后是兩宋,319年。因為沒有完成天下統一,所以釀成了靖康之變。但總體上維持了北宋+遼、南宋+金兩個100多年的和平時期。
元朝是個短王朝,和平維持了不到90年。然后是大明朝,又是一口氣統一了276年。朱元璋死后,第二任皇帝鎮不住,造成靖難之役,到永樂大帝才大放光彩,修北京城,修永樂大典,派鄭和下西洋。后面有土木堡之變,有張居正改革,但基本上是和平盛世。
明末農民起義,滿清成立,到清統一,大約動亂了30年。多爾袞實際上是清入關后的第一個掌權者,第二個是順治皇帝,早亡。康熙四歲登基,鰲拜、三藩亂了一通,但統一不可阻擋,一口氣和平了近150年,直到太平天國。之后同治中興,又存在了50多年,一共267年。
民國從1911年到1949年是38年。人民共和國在毛主席晚年經歷了10年動亂,但鄧小平撥亂反正。從1979年到2019年,40年間蒸蒸日上,盛世重現。
2019年新中國建國70年。
西漢70年是漢武帝元光2年,他在位才8年,對匈奴的大反擊剛剛開始。霍去病8歲,要10年后才顯風采。
唐70年是唐睿宗垂拱4年, 2年以后武則天才稱帝,25年以后才開始開元盛世;67年以后才是安史之亂;李白13年以后才出生;杜甫24年以后才出生。
北宋70年是1030?年,宋仁宗即位8年,仁宗盛世還有31年。據靖康之變還有93年。蘇軾 7年以后才出生。
大明70年是1438年,明英宗正統4年, 朱棣大帝剛剛過世14年。王陽明34年后才出生,距離張居正出生還有87年。
大清70年是1714年,康熙48年。乾隆皇帝才3歲,距離鴉片戰爭還有126年。
如果這個規律成立,我們這個盛世才剛剛開始,想想“李白”和“蘇軾”還沒出生,“乾隆皇帝”還在吃奶。
那么為什么會有這個規律呢?我們平時學歷史,一般總結王朝滅亡的原因是王朝末年皇帝昏庸,大臣腐敗,官逼民反,所以垮臺。真的嗎?
大明朝張居正改革是個非常有意思的案例。張居正開始掌權是1572年,那時大明朝已經過了202年。按理說,應該是皇帝基本不靠譜,該腐敗的也都腐敗了。但只用了10年,到1582年他死時,內部府庫充盈,對外任用戚繼光,北方安定,國家重新上了軌道。憑著這個積蓄,萬歷皇帝在朝鮮打跑了日本,平定了寧夏和云貴的叛亂,號稱萬歷三大征。而且除了統一稅制的一條鞭法,張居正沒有創新什么制度,只是提拔能干的人,把原有的制度認真執行,認真考核,國家就煥然一新。
天子流官體制非常有自我糾錯能力。因為宰相來源于民間,體制有新鮮血液。因為在宰相心底,有“為天地立心,為生命立命,為往圣續絕學,為天下開太平” 的政治理想。因為兩千年的實踐,有非常完備的治理工具箱,只要翻翻史書,解決問題的方法都在,只要用心去做就好了。
而且中國歷史上實現統一,只要不內亂,就不會亡國。兩晉是八王之亂給了胡人入侵的機會。兩宋沒有完成國家統一,給了蒙古人機會。大明亡于李自成。因為只要中國實現了統一,就像草原上的大象,雖然性格溫和,但太大了,除了自己,沒有天敵。
那么是什么力量讓和平解體,王朝覆滅哪? 答案是氣候。
竺可楨先生從古籍中找到蛛絲馬跡,寫了一篇論文《中國5000年來氣候變遷初步研究》。從中可以知道,中國歷史上幾次最大規模的社會動亂和四次小冰河期有密切關系,而不是吏治失敗引起的。殷商末期到西周初年是第一次小冰河期,東漢末年、三國、西晉是第二次小冰河期,唐末、五代、北宋初是第三次小冰河期。明末清初是第四次小冰河期。
穿越到崇禎年間,和平200多年,人口達到了1.2億,基本是土地承載的極限。氣候變冷,糧食產量下降而且持續40~50年,這完全超過了政府的救災能力。百萬級的饑餓流民造反,戰爭造成田地荒廢,饑荒不斷擴大。更多的流民,更大的戰爭,更大的饑荒。最后大家都卷進來,社會崩潰,神仙也沒辦法。這是內亂。更糟的是,北方變冷,游牧民族遭受白災,只有加大南下搶劫以圖生存,這是外患。因為沒有糧食,人們挖田鼠,造成鼠疫流行,十室九空,這是瘟疫。一個末世的完美風暴。
所以全球變暖不是好事,但如果全球變冷就是災難了。
另外的佐證是,中國的亂世和歐洲基本吻合。中國的漢對應羅馬帝國的盛世,羅馬帝國滅亡后的300年動亂,正好是中國兩晉南北朝的大動亂時期。1600年后的70年,歐洲叫凱瑟琳冰期,大家逃往新大陸。1604年,弗吉尼亞殖民地建立,五月花號1620年到波士頓,也許不是完全的巧合。1850年前后是另外一個寒冷期,中國是太平天國,歐洲是著名的愛爾蘭土豆大饑荒。
要解決治亂循環,最重要的是要靠科技解決糧食問題。
▍最好的制度是改革開放的制度
蘇聯解體前,弗朗西斯·福山提出了“歷史終結說”,認為人類可以有一個永恒不變的好制度。
冷戰四十年,大家都認為自己有正確的制度。改革開放剛開始時,也是姓資姓社爭論不休。
1978年鄧小平提出改革開放,英文翻譯成reform and open-door policy。我們開始也這么認為。不言的假設是改革有個終極目標,我們改到那個目標就勝利了。而且在很多人心目中,那個目標就是美國。直到川普把大家叫醒之前,我們還在下意識里認為,美國的今天就是中國的明天。
最近又在仔細讀《小平文選》,不斷有收獲。我認為改革開放應該翻譯成 Adaptation with an open-mind——用開放的心態去適應。 改革的核心是批判教條主義,世界在變,制度一定要不斷適應變化的世界,引領世界的變化。除了初心不變,其他沒有神圣不可改變的制度。 開放不是搞外貿,而是用開放的心態去學習。只要是有效的 制度就學習,不封 閉自大。所以社會主義可以又是市場經濟,所以大一統的國家可以有一國兩制。 改革是進行時,改革開放不是要改成某種制度,改革開放就是制度本身。因為世界在變化,今天再好的制度,不改革也會變成很壞的制度。
我們親身經歷了改革開放的力量。記得90年代初,如果你看世界主要的報紙,都有新聞說中國的國有銀行技術上破產了,不良資產超過40%,沒有風控系統。但是從1993年底開始銀行改革,到用外匯儲備注入資本金,四大資產管理公司不良資產剝離,到引進戰略投資人,到2010年農行最后上市。整個過程,國家一共投入了4萬億人民幣,2010年四大銀行國有股份市值大于4萬億。不但收回了全部投入,而且打造了世界最大的健康的銀行體系。過去40年這樣的事情每一個領域都在發生。從增值稅到股票市場,從科創板到移動支付。中國政府可以說是世界上最愿意改變的政府。
看到問題,研究答案,小規模試點,積累經驗,不斷改進,然后推廣。看到好的方法,不論出身,拿來主義。所以才有中國官員連續多年成批到新加坡學習,到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進修。一部無比龐大的機器,一個無比龐大的組織,以驚人的速度在改革開放中成長,變化。世界上總是有問題,我們總是用改革開放來解決問題。
西方來的朋友在上海的高樓大廈中看到黨旗飄揚,總是搞不清楚,中國到底是什么制度?因為在美國的語境中,充滿了姓資姓社的教條主義。按照教條主義,社會主義應該是死去的蘇聯和還在掙扎的古巴、朝鮮。
所以改革開放的精神是在大一統條件下克服僵化的希望。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改革開放就是制度本身。
▍中國的治理邏輯
今天我們說“百年大變局”,實際上,鴉片戰爭后的說法是3000年未遇之大變局。因為那是中國第一次碰到了一個比自己有指數級優勢的文明。不僅有軍事力量,而且有更好的生活方式,有更堅定的宗教信仰。就像我們碰到自己不能理解的事務一樣,過去150年中國人經歷了三個階段:
排斥——拒洋人于國門之外;
妥協——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洋務運動;
崇拜——全盤西化,從改良主義到共產主義百花齊放。
從紅軍長征開始,西方的思想開始和中國實踐相結合,一直到打贏內戰,到改革開放,越來越清晰,治理中國的方法不是從西方的書里來的,而是要從中國的實踐中來。 馬克思主義的理想和中國傳統的政治理想方向一致。中國共產黨利用馬克思主義的方法論,列寧主義的組織技術,探索了一條適應3000年不遇之變局的方法。 歷史證明歐洲工業革命帶來的領先,還是存在于技術層面而不是哲學層面。
從歷史傳承的角度,中國的治理邏輯可以概括為:
·?人本主義為信仰
·?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為政治理想
·?代表全體人民利益的天子制度
·?以公平考試選拔人才來實現公平和廣泛的代表性
·?流官制度保證組織的統一
·?類似統一戰線的鄉紳制度,團結體制外的力量
今天的中國在基本的治理框架上仍然遵循傳統的軌道,因為這是實現天下太平的唯一方法。但新中國對治理邏輯的升級是全方位的,而且在不斷迭代中。 從中國共產黨作為領導核心來代表全體人民的長遠利益,到引進市場經濟的理念和工具,到用改革開放來適應不斷變化的社會,探索不停。
“路漫漫其修遠兮,我將上下而求索”。我們要有信心,只要不改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初心,堅持改革開放的方法,中國就會不斷創新,為人類文明走出一條嶄新的道路。
我喜歡在山里跑步,越野跑讓我成了一個樂觀主義者。因為雖然有酷熱、嚴寒、風雪、疲憊、傷痛,但是只要有前進的方向,一步一步走就一定會爬上前面的高山,就會離溫暖的營地越來越近。
因為在荒野里只能繼續前行,悲觀不是選項。
▍ 后記
因為工作的關系,我總是要和世界各國的客戶和投資人打交道。酒過三巡,總是要面對一個問題,我管它叫“中國悖論(China Paradox)”?——為什么中國能在一個按理說隨時應該崩潰的體制下,取得了不可否認的成功?按照西方的政治經濟邏輯推理出來的中國,應該像蘇聯或古巴或北朝鮮,和現實的中國有天差地別的距離。
每次我都試圖用他們聽得懂的方式解釋,為什么中國的復興是歷史性的而不是偶然性的?為什么在中國的治理結構下,能夠實現和平、發展和共同富裕?為什么統一對中國如宗教般重要?為什么中國總能以腦洞大開的方式解決幾乎不可解的問題?為什么每年1.3億中國人出國,除極少數人(犯罪分子為主)外,基本都回來了,沒有人留在“自由世界”?
我發現大多數情況下,大家說著同樣的詞,但講著非常不同的意思。用西方的語境解釋中國的問題,讓世界誤解,讓中國人自己迷茫。 中國像一個成績優秀的學生,怎么表現都被周圍的人罵,因不被理解而越來越有挫敗感。
這些問題逼著我學習、思考。這組短文就是這些思考的總結。
孔子說:“有國有家者,不患貧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而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即來之,則安之。”用今天的話講,就是做好自己,朋友自來。畢竟成功的邏輯都是成功后總結出來的。
只要中國和平安定,繼續發展,實現共同富裕,中國的邏輯就會被世界理解、接受和學習。
本文為文化縱橫新媒體“歷史觀察”專欄特稿,原題為《中國的治理邏輯》。 感謝作者授權原創首發, 歡迎個人分享,媒體轉載請聯系本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