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李小云 | 中國(guó)農(nóng)業(yè)大學(xué)
【導(dǎo)讀】2022年的北京冬奧會(huì)、冬殘奧會(huì),為疫情與戰(zhàn)亂陰霾下的世界,注入一抹和平之光。這場(chǎng)體育盛會(huì),寄托著世界人民在困境中守望相助的期盼,也表達(dá)了當(dāng)代中國(guó)人促進(jìn)世界團(tuán)結(jié)友誼的愿望。
本文分析,冬奧會(huì)本質(zhì)上是一個(gè)中國(guó)向世界講述自己是誰(shuí)、講述自身與世界關(guān)系的平臺(tái)。中國(guó)試圖打開(kāi)一個(gè)全新的敘事空間,其中蘊(yùn)含著中國(guó)的新世界主義想象和探索中國(guó)式現(xiàn)代化道路的政治邏輯。
文章梳理了從馬戛爾尼訪華以來(lái),中國(guó)不同歷史階段為實(shí)現(xiàn)現(xiàn)代化而付出的努力。作者認(rèn)為,新中國(guó)成立以來(lái)的社會(huì)主義建設(shè),從一開(kāi)始就是一個(gè)新的現(xiàn)代化過(guò)程;客觀來(lái)說(shuō),這個(gè)過(guò)程,尚未完全解決困擾著中國(guó)現(xiàn)代化道路的政治、經(jīng)濟(jì)和社會(huì)文化的一致性問(wèn)題,仍有待探索和努力。
作者建議,國(guó)人有必要卸下長(zhǎng)期以來(lái)難以擺脫的“理智”與“情感”分離的沉重包袱,超越單純從中國(guó)和西方歷史實(shí)踐中尋找思想資源的規(guī)范路徑,立足實(shí)踐主義,直面新的現(xiàn)實(shí)和未來(lái),走出“特殊性”和“歷史終結(jié)”的范式困境,建構(gòu)推動(dòng)中國(guó)式現(xiàn)代化的普遍主義的思想和知識(shí)體系。
本文原載《文化縱橫》2022年4月刊,原題為《冬奧之喻:中國(guó)式現(xiàn)代化的歷史線索》,僅代表作者觀點(diǎn),供諸君參考。
冬奧之喻:中國(guó)式現(xiàn)代化的歷史線索
18世紀(jì)法國(guó)著名喜劇作家和文學(xué)家馬里沃(Pierre Carlet de Marivaux)在他的《爭(zhēng)議》一劇中有這樣一段對(duì)白——
Mesrin:你從哪里來(lái)?
Azor:世界。
Mesrin:你說(shuō)的是我的世界?
Azor:呵,這我倒不知,因?yàn)槲矣泻芏嗍澜纭?/p>
馬里沃的這段對(duì)白實(shí)際上是一個(gè)多元世界的隱喻。
如果說(shuō)法蘭西是“另類(lèi)現(xiàn)代性”思想搖籃的話,那么當(dāng)北京冬奧會(huì)開(kāi)幕式百余名兒童唱起主題歌《雪花》時(shí),伴隨著“千萬(wàn)你我,匯聚成一個(gè)家”的童聲旋律,一個(gè)個(gè)雪花“國(guó)家”圍攏成一朵人類(lèi)共同的雪花的宏大景觀,又何不可以看作是一個(gè)非西方國(guó)家進(jìn)入自己的“現(xiàn)代化”的宣言?
北京冬奧會(huì)開(kāi)幕式不僅是一場(chǎng)形體與自然交融的盛會(huì),更是一個(gè)中國(guó)向世界講述自己是誰(shuí)、講述自身與世界之關(guān)系的平臺(tái)。在立春時(shí)的相聚,意味著應(yīng)對(duì)疫情和世界不確定性的新起點(diǎn),以及一起面向未來(lái)的政治愿景;中國(guó)文明如黃河之水天上來(lái),但是黃河之水終要匯入大海,寓意著中國(guó)與世界融合的大勢(shì)所趨;開(kāi)幕式?jīng)]有以古裝呈現(xiàn),童聲合唱是歌劇式的,雪花舞蹈是芭蕾式的,展示了中華文明的開(kāi)放性和包容性;最后各國(guó)入場(chǎng)的先后順序既明示了中國(guó)遵行“國(guó)際慣例”的態(tài)度,也展現(xiàn)了中國(guó)堅(jiān)持“中國(guó)特色”的政治決心。如果說(shuō)2008年北京夏季奧運(yùn)會(huì)開(kāi)幕式更多是從“物質(zhì)”角度展示中國(guó)五千年的宏大文明歷史,讓世界了解中國(guó)的過(guò)去;那么,2022年北京冬奧會(huì)開(kāi)幕式則讓世界從更深層了解中國(guó)的價(jià)值觀以及中國(guó)走向未來(lái)的路徑。可以說(shuō),2022年北京冬奧會(huì)向世界展示了中國(guó)正在試圖打開(kāi) 一個(gè)新的敘事空間:在新世界主義的語(yǔ)境下,依照人類(lèi)命運(yùn)共同體的理念建構(gòu)“中國(guó)特色”的“中國(guó)的世界”與“世界的中國(guó)”的框架。所有這些都蘊(yùn)含著中國(guó)的新世界主義想象和探索中國(guó)式現(xiàn)代化之路的政治邏輯。
如果說(shuō),古代奧運(yùn)的精神在于消除古希臘城邦之間的戰(zhàn)爭(zhēng)帶來(lái)的破壞,以便建構(gòu)一個(gè)以古希臘文明為核心的世界,而在歐洲工業(yè)革命快速發(fā)展之后的現(xiàn)代奧運(yùn),是在世界格局發(fā)生劇烈變動(dòng)的條件下,希望通過(guò)奧運(yùn)精神凝聚以歐洲為中心的“現(xiàn)代文明”主體,那么,北京冬奧會(huì)開(kāi)幕式則寓意著中國(guó)對(duì)人類(lèi)文明新形態(tài)的向往。 中國(guó)人需要卸下長(zhǎng)期以來(lái)難以擺脫的“理智”與“情感”分離的沉重包袱,摒棄單純從中國(guó)和西方歷史實(shí)踐中尋找思想資源的規(guī)范路徑,立足實(shí)踐主義,直面新的現(xiàn)實(shí)和未來(lái),走出“特殊性”和“歷史終結(jié)”的范式困境,建構(gòu)推動(dòng)中國(guó)式現(xiàn)代化的普遍主義的思想和知識(shí)體系。
▍馬戛爾尼訪華:歐洲資本主義擴(kuò)張下的中國(guó)文化主體性
直到18世紀(jì),中國(guó)一直都是歐洲建構(gòu)的學(xué)習(xí)“榜樣”。伏爾泰說(shuō)“在道德上歐洲應(yīng)當(dāng)成為中國(guó)人的學(xué)生”,歐洲對(duì)中國(guó)普遍的印象是,中國(guó)人是世界上最聰明最有禮貌的一個(gè)民族。歐洲人基于中國(guó)的社會(huì)文化實(shí)踐得出的這一印象并沒(méi)有錯(cuò)。如果說(shuō),馬戛爾尼是第一個(gè)顛覆歐洲對(duì)中國(guó)印象之人的話,那么他傳達(dá)給歐洲的“中國(guó)”新印象恰恰是在資本主義物質(zhì)文明這面鏡子對(duì)照下的“中國(guó)”。這其實(shí)就是中國(guó)近代以來(lái)面對(duì)歐洲資本主義擴(kuò)張所出現(xiàn)的種種政治和社會(huì)文化糾結(jié)的背景。
17世紀(jì)以來(lái),中國(guó)還在封閉的環(huán)境中獨(dú)享天朝的昌盛,歐洲則開(kāi)始了改變世界格局的工業(yè)革命。工業(yè)革命所依托的資本主義生產(chǎn)方式,不僅推動(dòng)了歐洲內(nèi)部政治和經(jīng)濟(jì)社會(huì)結(jié)構(gòu)的巨變,同時(shí)由于資本主義不斷擴(kuò)大的再生產(chǎn)和對(duì)利潤(rùn)的追逐,產(chǎn)生了對(duì)原材料和海外市場(chǎng)不斷增加的需求。以英國(guó)為代表的歐洲資本主義的海外擴(kuò)張日趨強(qiáng)烈。實(shí)際上,直到明嘉靖年間,中國(guó)與歐洲一直有著密切的聯(lián)系。明嘉靖二年(1523年)嚴(yán)禁海運(yùn),廢除泉州和寧波市舶司,只存廣東司。清政府繼承明末閉關(guān)政策,不允許外國(guó)商人在廣東之外從事貿(mào)易。18世紀(jì)中葉以來(lái),國(guó)外商人“移市入浙”的趨勢(shì)日漸增加,資本主義向中國(guó)內(nèi)地的擴(kuò)張趨勢(shì)也日趨凸顯。由于清政府局限在廣州的通商政策不能滿足大英帝國(guó)對(duì)華貿(mào)易的需要,英國(guó)國(guó)王應(yīng)東印度公司的請(qǐng)求,于1787年(乾隆五十二年)派遣凱思·卡特為使臣,前往中國(guó)展開(kāi)交涉。凱思·卡特在途中病故,未能完成使命。五年以后,大英帝國(guó)又派遣馬戛爾尼出訪中國(guó),希望通過(guò)談判,敦促清政府取消對(duì)外貿(mào)易中的各種限制和禁令,從而打開(kāi)中國(guó)門(mén)戶,開(kāi)拓中國(guó)市場(chǎng)。但是,乾隆斷然拒絕了大英帝國(guó)的請(qǐng)求。
在今天融入全球化的語(yǔ)境下審視這一歷史事件,我們很容易得出大清王朝閉關(guān)自守、拒絕現(xiàn)代化的結(jié)論。馬戛爾尼提出的建議,除了要求在廣州附近劃出一塊地,任由英國(guó)人自由往來(lái)、不加限制這一明顯具有殖民意圖的建議以外,其他均屬可以談判的通商要求。因此,馬戛爾尼訪華的失敗被普遍看作是中國(guó)喪失了一次與工業(yè)文明接觸的機(jī)會(huì),也喪失了一次認(rèn)識(shí)世界和推動(dòng)中國(guó)現(xiàn)代化的機(jī)會(huì)。然而,在當(dāng)時(shí)中國(guó)還是歐洲“榜樣”,以及清王朝整體上還是一個(gè)和平且富有的國(guó)家的語(yǔ)境下,清王朝似乎更多地感受到大英帝國(guó)的領(lǐng)土擴(kuò)張以及對(duì)大清王朝統(tǒng)治的威脅。沈艾娣(Henrietta Harrison)認(rèn)為馬戛爾尼之行讓大清王朝直接感受到了英國(guó)對(duì)于中國(guó)的軍事威脅。實(shí)際上,當(dāng)時(shí)的清王朝已經(jīng)掌握了英國(guó)東印度公司獲得印度孟加拉邦統(tǒng)治權(quán)的信息,意識(shí)到英國(guó)在喜馬拉雅山外的威脅。因此,馬戛爾尼離開(kāi)北京以后,乾隆簽署一系列文件,指示各地嚴(yán)守口岸,提前備戰(zhàn),防止英國(guó)的侵略。同時(shí),乾隆要求各地稅務(wù)官員不準(zhǔn)收稅敲詐,不許對(duì)英國(guó)商船提高關(guān)稅,防止英國(guó)尋找借口發(fā)動(dòng)侵略。
很顯然,從乾隆為接見(jiàn)馬戛爾尼準(zhǔn)備英國(guó)相關(guān)資料時(shí)在地圖上找不到英國(guó)一事,可見(jiàn)大清王朝的封閉,加上乾隆年事已高的客觀現(xiàn)實(shí),大清王朝并無(wú)認(rèn)識(shí)世界、與歐洲接觸的迫切需要。相反,乾隆優(yōu)先考慮的是維護(hù)大清江山穩(wěn)定,防止外部侵略。但是,以中國(guó)失去與歐洲現(xiàn)代化相交的機(jī)會(huì),保護(hù)中國(guó)不被殖民的策略,最終也沒(méi)能改變中國(guó)淪為半殖民地的命運(yùn)。這一格局還留下了一個(gè)長(zhǎng)期困擾中國(guó)現(xiàn)代化的重要問(wèn)題:一個(gè)完整的中國(guó)政治文化體如何應(yīng)對(duì)西方資本主義擴(kuò)張?當(dāng)然,乾隆的遺產(chǎn)除了對(duì)世界無(wú)知的妄自尊大、維護(hù)大清江山的“私利”以外,或許在某種程度上也是一種文化保守主義的表達(dá),甚至可以說(shuō)是一種“文化自信”。為此,我們需要從更廣闊的語(yǔ)境出發(fā),將大清王朝統(tǒng)治者的“私利”和由其所產(chǎn)生的維護(hù)中國(guó)文化主體性的結(jié)果適當(dāng)剝離。這一剝離有助于我們?cè)趯ふ抑袊?guó)式現(xiàn)代化歷史資源的努力中,獲得更為客觀的線索。
▍從清末到五四:從“被動(dòng)現(xiàn)代化”到“積極現(xiàn)代化”的躍遷
源于草原民族的大清統(tǒng)治者,依靠他們的長(zhǎng)矛利劍和火繩引爆的槍炮不僅征服了中原,也抵制了沙俄。但是在馬戛爾尼離開(kāi)北京的半個(gè)世紀(jì)之后,大清王朝的長(zhǎng)矛利劍終究沒(méi)能抵御住大英帝國(guó)的連發(fā)槍?zhuān)袊?guó)出現(xiàn)“落后”和“先進(jìn)”之爭(zhēng),有了我們今天講的“現(xiàn)代”。在這個(gè)過(guò)程中,像郭嵩燾這樣從制度層面直面中國(guó)落后狀況的少數(shù)精英,以李鴻章為代表的開(kāi)明統(tǒng)治者和社會(huì)精英,均將中國(guó)的落后歸結(jié)于“器物”的不發(fā)達(dá)。1872年,李鴻章操辦了中國(guó)第一家“國(guó)營(yíng)企業(yè)”——輪船招商局;1886年,方舉贊和孫英德在上海建立了中國(guó)第一家民族資本工業(yè)企業(yè)——發(fā)昌機(jī)器廠。如果說(shuō)鴉片戰(zhàn)爭(zhēng)迫使中國(guó)面對(duì)“現(xiàn)代”,那么洋務(wù)運(yùn)動(dòng)和戊戌變法則可視為中國(guó)開(kāi)始“被動(dòng)現(xiàn)代化”的開(kāi)端。這種“現(xiàn)代化”的被動(dòng)性發(fā)育出了“中體西用”的思想。咸豐十一年(1861),馮桂芬在《校邠廬抗議》中提出了“以中國(guó)之倫常名教為原本,輔以諸國(guó)富強(qiáng)之術(shù)”的主張,奠定了至今仍然影響著中國(guó)現(xiàn)代化的“中學(xué)為體,西學(xué)為用”?的應(yīng)對(duì)策略。“中體西用”的主張,是中國(guó)封建主義文化和西方資本主義文化結(jié)合的產(chǎn)物。這一思想一方面顯示了中國(guó)文化在西方資本主義文化強(qiáng)大沖擊下的韌性,另一方面也是面對(duì)強(qiáng)大西方的某種無(wú)奈。這一思想在實(shí)踐上的失敗,可以歸結(jié)為中國(guó)被動(dòng)進(jìn)入“現(xiàn)代”在物質(zhì)和思想兩個(gè)方面的生產(chǎn)能力的儲(chǔ)備缺失。
從當(dāng)代中國(guó)在現(xiàn)代化方面取得的長(zhǎng)足進(jìn)步的角度看,固守“傳統(tǒng)”、匆忙應(yīng)對(duì)現(xiàn)代挑戰(zhàn)的策略,必然會(huì)導(dǎo)致如王國(guó)維所講的“可愛(ài)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愛(ài)”這種“心智”和“天理”的裂痕。盡管我們可以天真地假設(shè)“中學(xué)為體”并非全是服務(wù)于穩(wěn)固大清王朝統(tǒng)治的思想產(chǎn)品,而是也接受了“器物現(xiàn)代化”的積極意義,但我們依然不能否定這一范式的本質(zhì)并非真正意義上的推動(dòng)現(xiàn)代化,而是一種處于守勢(shì)的功利性應(yīng)對(duì)策略。這也就注定了即使擁有了“先進(jìn)”的“器物”(如北洋艦隊(duì)),中國(guó)仍無(wú)法逃脫失敗的命運(yùn)。這一教訓(xùn)對(duì)于我們今天推動(dòng)中國(guó)式現(xiàn)代化,仍然有著十分重要的現(xiàn)實(shí)意義。
清末以“中體西用”被動(dòng)性應(yīng)對(duì)危機(jī),產(chǎn)生了一系列政治文化后果。首先是“理智”和“情感”的分離。面對(duì)西方現(xiàn)代化的沖擊,中國(guó)人經(jīng)歷了從無(wú)奈到逐漸適應(yīng)、接受,繼而主動(dòng)追求的過(guò)程——這中間又不免承受數(shù)典忘祖的道德責(zé)難。慈禧曾訓(xùn)斥光緒帝騎自行車(chē)是“一朝之主當(dāng)穩(wěn)定,豈能以‘轉(zhuǎn)輪’為樂(lè)”。其次是政治與文化邏輯的分離。資本主義沖擊下的應(yīng)對(duì)策略通過(guò)“本”和“用”的功利主義邏輯,使面對(duì)現(xiàn)代化時(shí)需要的政治和文化的一致性發(fā)生了斷裂,力圖挽救統(tǒng)治者視角的“政體”和“傳統(tǒng)”。五四運(yùn)動(dòng)的爆發(fā)徹底動(dòng)搖了導(dǎo)致這些斷裂的政治和社會(huì)文化基礎(chǔ)。五四運(yùn)動(dòng)把“新”的國(guó)民生活敘事投放到中國(guó)人的價(jià)值中,選擇現(xiàn)代不再是無(wú)奈,而是一種內(nèi)化的精神。五四運(yùn)動(dòng)的核心是新文化運(yùn)動(dòng)。五四所倡導(dǎo)的文化既是“傳統(tǒng)”的,又不是過(guò)去的“傳統(tǒng)”,而是“新文化”。五四運(yùn)動(dòng)是在反對(duì)封建主義和帝國(guó)主義的語(yǔ)境下發(fā)生的啟蒙運(yùn)動(dòng),其發(fā)生的背景和激發(fā)的思想資源決定了其對(duì)中國(guó)現(xiàn)代化的意義。五四運(yùn)動(dòng)在理論上完成了中國(guó)人進(jìn)入現(xiàn)代所面臨的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精神與物質(zhì)、政治與文化的一致性的建構(gòu)。無(wú)論中國(guó)的民族主義者還是中國(guó)共產(chǎn)黨,都是五四運(yùn)動(dòng)的學(xué)生。從這個(gè)意義上講,相比之前的“被動(dòng)現(xiàn)代化”,五四運(yùn)動(dòng)標(biāo)志著中國(guó)進(jìn)入“積極現(xiàn)代化”的階段,推動(dòng)了中國(guó)進(jìn)入屬于自己的“現(xiàn)代化”。
當(dāng)然,五四運(yùn)動(dòng)雖然從思想上打通了精神和物質(zhì)、政治和文化、集體與個(gè)體、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的聯(lián)系,但是這都是觀念性的想象,并沒(méi)有解決中國(guó)現(xiàn)代化的道路選擇問(wèn)題。與近代歐洲現(xiàn)代化不同的是,中國(guó)進(jìn)入近代后面臨著巨大的生存危機(jī)。“中體西用”無(wú)法拯救中國(guó),中國(guó)需要在高度壓縮的時(shí)空中展開(kāi)走向現(xiàn)代化的思想建設(shè),這對(duì)文化和政治的貫通和統(tǒng)一提出了相當(dāng)高的要求,從而使得中國(guó)的現(xiàn)代化進(jìn)程異常的艱難。
五四運(yùn)動(dòng)最重要的遺產(chǎn),是推動(dòng)知識(shí)精英們達(dá)成了中國(guó)的現(xiàn)代化需要將政治、經(jīng)濟(jì)和社會(huì)文化統(tǒng)合成一個(gè)一致整體的共識(shí)。但是,這個(gè)一致性的實(shí)踐形態(tài)在五四之后出現(xiàn)了兩條道路的分野,即資產(chǎn)階級(jí)民主革命和社會(huì)主義革命。兩者雖然都接受了五四反帝和反封建的遺產(chǎn),但是兩者卻接受了不同的“西方”思想。五四運(yùn)動(dòng)發(fā)生的同一年,孫中山將他寫(xiě)的中國(guó)的國(guó)際發(fā)展項(xiàng)目的建議寄給美國(guó)商務(wù)部長(zhǎng)瑞德菲爾德,他在致瑞德菲爾德的信中說(shuō),“威爾遜總統(tǒng)建議建立國(guó)聯(lián)結(jié)束戰(zhàn)爭(zhēng),我建議通過(guò)與中國(guó)發(fā)展的合作和互助結(jié)束貿(mào)易戰(zhàn)”。孫中山?jīng)]有得到預(yù)期的支持。五四運(yùn)動(dòng)給予孫中山極大啟發(fā),推動(dòng)資產(chǎn)階級(jí)民主革命走向愛(ài)國(guó)和反帝的主戰(zhàn)場(chǎng),為中國(guó)民族資本主義發(fā)展奠定了基礎(chǔ)。但是,資產(chǎn)階級(jí)民主革命忽視了占中國(guó)大多數(shù)的農(nóng)民的土地權(quán)益,其革命主張和實(shí)踐無(wú)法體現(xiàn)中國(guó)大多數(shù)人口的基本訴求,因此最終走向失敗。
中國(guó)共產(chǎn)黨則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理論,創(chuàng)造性地把解決農(nóng)民的土地問(wèn)題作為其革命主張,推動(dòng)中國(guó)完成社會(huì)主義革命。革命之后的社會(huì)主義建設(shè),面臨著由于資本主義發(fā)展不足造成的生產(chǎn)力水平低下的挑戰(zhàn)。為了應(yīng)對(duì)這一挑戰(zhàn),中國(guó)共產(chǎn)黨形成了基于現(xiàn)實(shí)主義的社會(huì)主義初級(jí)階段理論和社會(huì)主義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思想,并以此推動(dòng)了史無(wú)前例的改革開(kāi)放,取得了讓中國(guó)成為世界第二大經(jīng)濟(jì)體的成就。自新中國(guó)成立以來(lái)的社會(huì)主義建設(shè),從一開(kāi)始就是一個(gè)新的現(xiàn)代化的過(guò)程。客觀地講,這個(gè)過(guò)程并沒(méi)有完全解決困擾著中國(guó)現(xiàn)代化之路的政治、經(jīng)濟(jì)和社會(huì)文化的一致性問(wèn)題。
▍“世界的中國(guó)”:新時(shí)代的中國(guó)現(xiàn)代化進(jìn)路
如果說(shuō),從中國(guó)進(jìn)入現(xiàn)代以來(lái)的生存性應(yīng)對(duì),到被動(dòng)的現(xiàn)代化,再到社會(huì)主義的新的現(xiàn)代化,都主要聚焦“中國(guó)”的話;那么,進(jìn)入新時(shí)代以來(lái)的中國(guó)現(xiàn)代化進(jìn)程,將不得不考慮“世界的中國(guó)”。“世界的中國(guó)”,面臨著西方中心主義的挑戰(zhàn)。在理論上,中國(guó)已提出人類(lèi)命運(yùn)共同體和人類(lèi)文明新形態(tài);但在實(shí)踐層面,如何超越西方基督教和自由主義教義下的普世主義,仍然困難重重。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所帶來(lái)的不平等,雖然通過(guò)脫貧攻堅(jiān)有很大的緩解;共同富裕的目標(biāo),也為解決不平等問(wèn)題提供了明確的方向;發(fā)展國(guó)有經(jīng)濟(jì)和規(guī)范資本的過(guò)度擴(kuò)張,也確保了社會(huì)主義基本制度的基礎(chǔ);但與此同時(shí),個(gè)體和市場(chǎng)機(jī)制之間的張力一直存在。應(yīng)對(duì)氣候變化和推動(dòng)綠色發(fā)展與技術(shù)創(chuàng)新,也是中國(guó)現(xiàn)代化過(guò)程面臨的新挑戰(zhàn)。從歷史和現(xiàn)實(shí)的角度講,中國(guó)式現(xiàn)代化一方面是一個(gè)建設(shè)新的政治、經(jīng)濟(jì)、社會(huì)文化一致性的“中國(guó)問(wèn)題”,另一方面也是一個(gè)建設(shè)人類(lèi)命運(yùn)共同體的新世界主義的問(wèn)題。從這個(gè)意義上講,中國(guó)式現(xiàn)代化的道路將比以往任何時(shí)期都要艱難。中國(guó)式現(xiàn)代化面臨著否定“傳統(tǒng)”與延續(xù)中國(guó)的文明,否定西方中心主義與吸收西方文明的精華,以及“中國(guó)特色”與西方普世主義等復(fù)雜問(wèn)題,雖然這些問(wèn)題并不必然二元對(duì)立,但是必須承認(rèn)存在張力。中國(guó)式現(xiàn)代化依然是一個(gè)長(zhǎng)期的探索,其關(guān)鍵是如何建立起各種要素協(xié)調(diào)一致的“以人民為中心”的現(xiàn)代化。
這將是一個(gè)復(fù)雜的、高難度的系統(tǒng)工程。中國(guó)的政治實(shí)踐只能靠探索,而中國(guó)的社會(huì)科學(xué)家則需要據(jù)此重構(gòu)相應(yīng)的思想和知識(shí)體系,這對(duì)中國(guó)人民的政治和社會(huì)文化智慧提出了更高的挑戰(zhàn)。
本文原載《文化縱橫》2022年4月刊,原題為《冬奧之喻:中國(guó)式現(xiàn)代化的歷史線索》,歡迎個(gè)人分享,媒體轉(zhuǎn)載請(qǐng)聯(lián)系本公眾號(hà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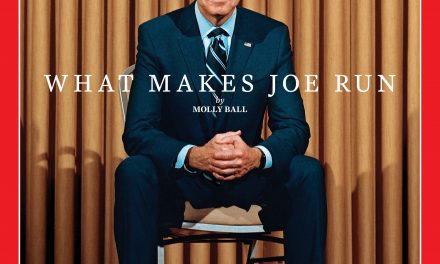




志-150x150.jpg)
-150x150.jpg)
